TIME:2018-08-15
2018年7月15日下午两点,熬吧读书会与凤凰网合作为胡竹峰举办《中国文章》新书首发暨文学分享会,韩少功、何立伟、水运宪、蔡测海等多位著名作家参与对谈,活动主持人为熬吧读书会丛林。以下为文学分享会对谈实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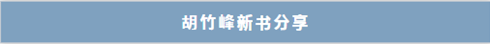
胡竹峰:
其实出来做活动很多场了,但是第一次这样紧张,因为台下各位嘉宾都是我的前辈。我差不多是读何(立伟)老师的书长大的,昨天晚上见到他特别高兴,然后今天他特别客气,还为我画了两幅画,待会儿可以向各位展示一下。
这本《中国文章》,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一本散文选集,我写散文随笔有10多年了,我希望在此之前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小范围的总结,所以就出了这么一本选集。这本书分了三集,第一部分我主要谈的是中国文章衍生来的一些话题,包括我读鲁迅、读《章衣萍》、读《牡丹亭》等作品的一些札记,还有独立的一些中国碑帖的随笔都在里面。第一篇文章叫《中国文章》。有朋友跟我讲,说这个书名有点大,我现在看这本书,觉得确实有点大,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写的文章就是中国文章,其实中国文章是一个名词,是一个泛的概念。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?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作家也好、文人、学者、各类文字工作者也好,好像把文章的概念缩小了。我们现在谈到散文,好像说的就是抒情散文,那种小情小调的散文,甚至还有一种争议,说我书中有些内容不是纯散文,所以我想打破这样一个概念。我们现在回过头看《古文观止》,会发现里面抒情的散文很少。我们再看古代文人的一些文集会发现,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抒情散文是很少的,可能有的人一辈子就写了那么三五篇,因为那些文章成了名篇,到处选,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。还有些人读书读的是选本,就觉得苏东坡写的就是《赤壁赋》、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到张岱,就觉得他写的就是《湖心亭看雪》,会大量屏蔽中国传统意义的文章。
有人说你是不是想恢复传统的中国文章,我说这打哪儿恢复,因为传统从来没有断过。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,都是写得一手特别好的中国文章,所以我不是恢复这个传统,我是向传统致敬,向传统靠齐。因为我觉得一个写文章的人,一个人是很渺小的,只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来做这件事,你的文脉的流传痕迹才能更长,你的文章也没那么容易被时代所阻隔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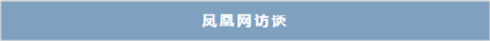
凤凰网记者:胡竹峰先生您好,您觉得文学文章的作用是什么?文学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?
胡竹峰:
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老前辈、台湾的一个著名诗人聊天,我问他,你怎么看待你这辈子的文学创作?他想了想,说还是立言。他说,我写这么多东西,我做的是立言。其实这种念头在我们心里是有的,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敢讲这种话,因为自己太年轻了,像水运宪老师、韩少功老师、何立伟老师还有在座各位前辈,立言的话,他们敢想,我们不敢想。但是这种念头我们有,就是觉得不要虚度自己,要对得起自己,此其一。此其二,我想人都是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,人有很多的欲望,饮食的欲望、看风景的欲望、要表达的欲望,我觉得写作是生命的投入,我写这本书投入了我的生命,但我更看重的是我个性光芒的发挥,这本书有我个性的光芒,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
我觉得文学可以让我过得更从容一点,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坦然,可以让我们更从容、更通透,到最后会有一种很圆融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们谈到文学大师,会说他是位“真人”,“真”这个字很难,明心见性很难,要心明了才能见性,我觉得这是文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最美妙的地方。
凤凰网记者:你在一篇文章中写到:写作像是黑夜的长啸。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?
胡竹峰:
那是我的第一本书,那时候年轻。我今天可能会有一点变化,温柔的变化。为什么说黑夜的长啸,“啸”的时候需要有人回应啊。如果把这句话放在韩老师、何老师、水老师身上,就未必合适了,因为他们写作的时候无所谓别人回声不回声,他们有了足够的自信,自己知道自己是谁,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但是我当时才20几岁,特别想要有回应,特别希望你的书有人看,听到有人说好,如果有人说不好,就会特别在乎,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里面,这其实就是一个求其友声的意思。
凤凰网记者:您的作品中,中国风格是很明显的,在13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颁奖词里面就写到:中国文章呼唤中国精神,胡竹峰,以他的文字秉承了这种精神。您觉得,什么才是中国精神呢?
胡竹峰:
“中国精神”这个话太大了,那我就谈谈中国文章的精神吧。中国文章的精神就是山川草木的精神、是水墨的精神。我们看整个东方文学的审美,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,比如你去西方旅游,西方是不会给你苏州园林那种感觉的,不会给你书画水墨的感觉。据说张大千见过毕加索。毕加索对中国水墨特别推崇,说有中国人到巴黎去跟毕加索学画,毕加索特别愤慨,说你们真傻,你们东方的水墨那么好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,向传统靠,写出那种水墨画的感觉。中国有很多传统,古典文学的传统、民间的传统,我更希望的是向古典精神靠。什么是古典精神呢?我的理解可能跟一般的理解有差别,刚刚谈到了,是山川草木的精神、是自然的精神,还有很手工的那种精神。还有呢,我有个偏见,我特别害怕一个人过于在文字里面谈思想,如果你的思想一定要浮在文字的表面上,让别人一看就把你的思想看出来了,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好。我觉得思想要沉在文章里面,要揉进去,就像和面一样。水跟面是融为一体的,不能分开,分开的话你就做不成面了,也做不成水饺。这是我的一个偏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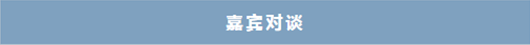
何立伟:
竹峰是安徽人。安徽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文脉的地方,像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方苞、姚鼐,然后到民国,有胡适、陈独秀,可以说我们现在写白话文基本就是从他们那个时代开始的,这个文脉在一个地方是有延续的。这种延续,在一个80后身上得到这么好的体现,所以我读胡竹峰的文章的时候,从心里面感到一种由衷的高兴,我高兴中国的文脉,在今天有一种正道传承。
竹峰的文章有一种无古无今的东西,是一种美妙的阅读体验。能在今天的时代,体会到古代文人写文章的态度、生活的态度、审美的把玩、日常的态度。
昨天跟胡竹峰见面,我觉得聊得还比较投情,没什么障碍,在对真正好文章的理解上,我跟他的看法一致,我们都觉得好文章是什么?叫“锦绣文章”。胡竹峰的文章就是在朝着锦绣文章的道路上走,他是完全有能力写出真正的锦绣文章。
我今天很高兴,吃饭之前特意画了两幅画送给他,而且是为他量身定制的,给大家献个丑(拿出画)。这幅画画的是一只老鼠在书匣上面啃书,我写的是“竹峰属鼠又好读书,因作老鼠啃书图把赠也”,这边是“好书宜细啃”,像老鼠一样慢慢地啃。胡竹峰就是一只好老鼠,在慢慢啃书。还有一幅,胡竹峰有一本书叫《民国的腔调》,我特别喜欢。这个我画的叫“民国样范”,我想象的是鲁迅,但是我只画了眉毛和胡子,叫眉毛胡子一把抓,没有眼睛,没有鼻子。“样范”是我们湖南的方言,就是模样。这边写的小款是“竹峰小兄,民国腔调大著,吾据此作小图,以呼应耳”。都是给竹峰的量身定制,表达老少文人间的文墨交往。礼轻情意重,算是我对后辈的一种相惜吧。

竹峰这本书里面,谈中国文章谈到庄子、司马迁,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庄子,然后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小说家等等,他读书的这些喜好、选择、标准,我都非常喜欢。他说他读鲁迅的文章,首先最喜欢的是他的“跋”。鲁迅的序跋是精彩到极点的,比正文还好看。中国古代文人,序跋都是写得非常漂亮的,轻松嘛,写序跋的时候用不着端起来,有一种很轻松的驾驭。好东西都是最轻松的,好东西都是在放松的状态下才有的神来之笔,紧张不可能有,端起来不可能有神来之笔。
而且我觉得竹峰的修养非常好,我看他读很多的经典都是一读再读,而且是深读,读出来的东西有他自己的实践。竹峰谈碑帖,书法,这些感受,和我们写文章是一回事,当你用审美的眼光去打量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时候,其实就是一致的。中国的书法、中国的文章,都是一样的,留白、浓淡、刚直等,道理都是一样的。
还比如胡竹峰说读鲁迅的小说之前,最好是先读一读鲁迅的传记,因为你的身世,是你文章的底色。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解人之语,读书读通了。当你了解这个人,回过头再去看他的文章,你就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最近还重读了一遍《从文自传》,我早就读了,但是我又拿出来读了一遍。所以,胡竹峰在读书的时候,非常有自己的心得,这种心得不受到外来影响,都是基于自己的审美判断。
他提到了中国的文章要有墨趣。墨趣是什么,比如说齐白石的虾子,他的笔墨把虾子的那种透明感画得特别的形象,充满了笔墨趣味,这种修炼,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超越的。现在的大多数文章都没有墨趣,他们不知道语言可以像笔墨一样出彩,他们不知道语言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生动、叫活色生香。我觉得好的画、书法必须具有两种气息,一种是才子气,才子气是先天的;还有一种是后天的,叫书卷气。书卷气决定你的厚度,胸无点墨的人不可能作出好画。有了这两种气息,无论是在书法、绘画还是写文章,你都会是不俗的,都是有品位的、有品相的。我读胡竹峰的文章,我特别喜欢第一集,非常好,非常有神韵,而且要言不烦,可以感觉到这两种气息的存在的。他把握文字、语句都非常准,好的文章是有一种娓娓的、从容的语气。像他这样的少年,能有这种从容、自信,不容易。好的文章就是跟人聊天。
丛林:我想问胡竹峰先生一个问题,刚刚何立伟老师也说到了,说你的文章非常好,我看你的书也有非常震惊的感受,觉得你这么年轻,能有这么惊人的阅读量,先秦诸子、魏晋碑帖、尺牍、人物、山水,什么都能够以历史贯穿的脉络融合在一起,那么我想请问,除了海量阅读的积累之外,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我们阅读的悟性?
胡竹峰:
我觉得这是与自己心性有关的东西,当阅读达到一定量的时候,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就会被拉出来,会发生裂变,会产生另外一个自己,会让你吓一跳的自己。而且我现在越发有一种感受,就是文学的东西未必要在文学圈里面找,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奇怪的书,看了很多古典的书,像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农政全书》、《天工开物》这种技术类的书,写这些作品的都是大人物,大人物写什么都好,《齐民要术》绝对是顶顶好的,绝妙的小品文,看这种书可以让我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个性。再比如我们谈到何立伟老师怎么写东西,他在读沈从文、读汪曾祺,那么汪曾祺擅长写小品文,喜欢读鲁迅,鲁迅又读什么书,你顺这个脉络往上走,你可能就会打通,我觉得这个很关键,就是要读你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书,这么一条线上去。文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,它不是一条大河波浪宽,它有一个断断续续,有一个线索,你找到这根线把它连起来,你可能就会接通一些东西。
我还想到一个问题,就是我现在可能还算年轻,但是在我写散文的时候,有种年纪凭空增长30岁的感觉,就是在那么一刹那,会突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。然后我觉得,好的文章啊,还是需要一种旧气,要用怀旧的笔调来写,才会有一种惘然感、怅然感。
丛林: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,您在《中国文章》这本书里面提到了文章的风致,说好文章就是一段好风致。那我想请问您,您觉得哪些文章是有好风致的?我们要怎么去练就文章的好风致?
胡竹峰:
我是这样想的,就像一个女人一样,如果又漂亮又气质好,那可以说是风致。文章是要韵味的,风致就是一种韵味。像苏东坡的、张岱的、沈从文的,都是好风致,就是刚刚谈到的锦绣文章。其实还有些文章写得特别好的人,比如周作人、孙犁,他们写的文章也很好,但应该不算是风致,是另外一种美,有一股淡气,一股憨气,那是另外一种美。
丛林:水老师,您也上来谈一谈好不好?
水运宪:
我觉得胡竹峰是一种现象,令我们老一辈作家非常兴奋的一个现象,我提前看了很多胡竹峰博客里的文章,还真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,感觉他接触的这个面非常广。刚刚竹峰也说到了,经历是一个人文章的底色,也就是身世。胡竹峰今年34岁,我大你36岁,所以我们写作的底色,就是我们自身的经历,而像你们这种类型的年轻作家,更多的是基于阅读,海量的阅读。在翻看了胡竹峰的博客之后,我就特别想看他的一本书,那就是《民国的腔调》,对这类文章特别欣赏,没想到一个80后的年轻人,文章能够写到这样炉火纯青,希望胡竹峰以后能够写出更多的好书。

丛林:我想问何老师一个问题,我是在10年之前就看过您的著作《大号叫人民》,描绘市井生活和小人物都非常有情味。有时候我就想,我们也在市井中生活,为什么我们发现不了那么多有趣味的东西呢?您这种比常人更灵敏的触角,是天赋的秉性?还是后天也可以训练呢?
何立伟:
可以训练。《大号叫人民》是我在北青报开专栏时候写的,都很短,2000多字写一个人。2000多字把一个人物写好写活其实很不容易,前提就是我对我写的人太熟悉了,都是我身边的人。好东西并不需要采风,采风意味着你去写你不熟悉的东西。好作家写得好的东西都是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。昨天还同胡竹峰聊韩少功的《山南水北》,那就是韩老师非常熟悉的生活,韩老师有半年呆在那个地方,好作家写得最好的一定是自己最熟悉的东西。就像很多摄影的,认为拿着相机跑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拍到有价值的东西,其实在家里就可以拍到无穷的东西,只是不善于发现。生活其实到处都充满了形式美,日常就是美 ,我喜欢日常的美 。所以《大号叫人民》里面,我写的都是日常,我喜欢日常的东西。
丛林:韩老师您好,您一路赶过来辛苦了。我知道胡竹峰的《中国文章》是您给写的序,您把他定义为“重建中国文章传统审美的可贵立言”,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。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一评价谈谈您对胡竹峰先生文章的印象?
韩少功:
首先说一声对不起,今天到晚了,但我的态度是最好的,我开车开了三个多小时,高速路上出了点状况,在大太阳下晒了好久才来到这里。
说到你刚刚问的问题,原先我跟年轻一代也讲过这么一些话,我说你们跟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也聊不到一块儿去,年轻人写的东西都很长,我曾经碰到一个年轻人跟我说:韩老师,你看看我的作品。然后给了个U盘给我,我以为是两篇散文或者是两首诗,一插进去,四个长篇,我吓死了(笑),可见现在年轻人创作能量之大。比如现在的网络小说作家,动辄几千万字,但是竹峰他不这样,他是年轻人中的异类,他写的都是很精致的东西。在内容上跟我们老家伙比较接近,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下,去吸收有益的一些东西。
至于说到他的传统美学,这又是竹峰的一个特点,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实践和理论都有很深刻的体会,这又和很多年轻人不一样。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应该都是进大学,读了文学理论,我们这些文学理论说老实话,基本都是西方舶来品,比如说我们的文学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几大块;然后三要素、主题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、写作风格几大块,我们老祖宗都不谈这个的,我们这些学科的基本面貌基本都是西方照搬过来的。我们学到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古典主义、批判现实主义等等,全是西方概念。我们中国老祖宗谈文章不谈这些东西,我们谈的是像王国维说的“有我之境、无我之境”,我们的《文心雕龙》谈趣味、意境、神韵,谈这些。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那些都是西方的脑子,在这点上,我就觉得竹峰非常可贵。他写文章,完全遵从我们老祖宗的传统,谈墨趣、谈风致。
当然,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好好学,但是不能光学习这些,我们自己的审美传统,丰厚的审美经验丢失了就太可惜了。而且我特别害怕,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文科博士硕士,完全就是西化的脑袋,西化的东西都没学好,就学了一脑子的标签,一脑子主义。说一点冒犯某些青年朋友的话,有一些做文化版面的编辑脑子比较简单,他们经常对有些报道、评论就是一脑子的标签贴来贴去,一个女作家出了新作品,往往要给她贴个标签“女权主义”。她是女权吗?女权在哪儿呢?什么是女权呢?骂男人被当成一种时髦,这种就太可笑了。写社会现实,就给他贴个“批判现实主义”,谁要是写到社会的阴暗面的,就是批判现实主义。哪个作家写作品不写一点不平之鸣呢?肯定都有一点不平之鸣、悲愤之言的,把这些个标签从古贴到今,从中贴到外,有什么道理呢?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反而我们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写得好不好,写得有没有韵味,有没有审美,这个字用得巧不巧?根本不去注意,这些方面都不关注,变得很大条,神经变得很粗糙,就满足于几个主义,贴几个标签就完了,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文科教育带来的一个恶果,对文学的口味都变得极其的恶劣粗糙、不得要领。所以竹峰的这本《中国文章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的新的视角、新的方法,就是我们看一篇文章,它的妙处在哪儿?怎么去品味它?所以为什么说这本书是重建中国美学传统的审美立言。

丛林:胡竹峰先生我再问您一个问题,也好让韩老师先喝口水。刚刚韩老师讲到,中国传统的审美跟西方的审美是不一样的,你在文章中也提到,中国的文章是“墨戏”,有“焦浓重淡清”之别,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文章的这个墨性?
胡竹峰:
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,不能从前到后都是一个笔调,所以有时候需要有这种焦墨或者淡墨,这是一种节奏感吧。我觉得文章只要超过300个字,就要有节奏感,如果没有的话,文章就会很平淡。清朝袁枚说过一句话叫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。
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到读鲁迅也是一样的,鲁迅有些文章其实是没道理的,但是他的词用得太牛了,把道理给夺过来了,他就有道理了。比如说鲁迅在写《秋夜》的时候,有这么一句话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我就觉得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就是一种好玩的心性。我记得韩老师《马桥词典》里面有一个人,打农药中毒,肿的一塌糊涂,后来中毒更深,就不肿了,不用戴面罩了,手也不肿了,头也不肿了,但那个人吐一口气,蚊子都死了、苍蝇都死了。那肯定是假的,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墨趣。韩老师的文章也是有“浓淡”的那种感觉。
我们在谈中国书法的时候,一幅字,一个笔画,要讲究墨的深浅,一个人也是一样,一辈子如果是一种状况,那多糟糕。中国现代文学馆里面,有一座郭沫若的雕像,我觉得把郭沫若塑造得太委屈了,把郭沫若塑造成双手举起来的呐喊的状态,就像是他一辈子就是这么一种双手举起的状态,多累呀。其实写文章也是一样,不能保持在一种腔调、一种状态,还是要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。
丛林:谢谢。您刚刚也反复提到韩少功老师的《山南水北》、《马桥词典》。韩老师这些书,在座各位可能同我一样,都早就读过的,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感觉元气特别充沛,淳朴自然而姿态横生,既醇厚又轻灵,所以我想请韩少功老师谈一谈,我们写文章时,要怎么处理好这种轻与重、神与骨之间的关系呢?
韩少功:
你的这个问题太深奥了。首先有一点,我跟立伟的观点是一致的,就是要写自己熟悉的、了然于胸的东西,我不太相信作家的那种过于夸大的自我想象力,我一般作品中原型人物的比例有7成,3成是靠虚构、想象。还有就是写东西要有情感,要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,这个时候就可以写得好一点了,也就是你说的元气充沛一点。像谈恋爱,你要有话可说,见面不吐不快,如鲠于心,这个时候写出东西就会很自然。写作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种喷涌的感觉。有些作家产量很高,但是写东西进入了职业的一种状态,职业化的谈恋爱就不是谈恋爱,只能说是三陪,她们是随时可以卖弄风情,表演一种爱,很多作品一嗅就知道,是不是真实的情感。但是作家也很为难,一辈子就那么点生活阅历,像我们都六七十了,你看我们这些老头子再恋爱一次也不容易啊,所以说写作要保持这种很充沛的情感,是不容易的。但是年轻人一定要充分尊重自己的情感,一定要让自己时刻处于一种写作的恋爱的状态,一种不说不快的、饱满、心里话要喷出来的状态,这就是要出好作品的征兆。
胡竹峰: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文章的诗意。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诗意,他的哲学性思想性可能会见长,但他的文学性可能就没有了。两位老师怎么看。
韩少功:
我没发表过诗,但我特别崇拜诗人。我觉得诗是文学中的文学,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。古代有《诗经》,没有什么小说经,散文经,诗是可以达到经的高度的。诗是小说灵魂的东西,好的散文,好的小说,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都有诗性在里面。
胡竹峰:韩老师何老师两位老师,您是我们的前辈,你们现在写文章也没有放弃文采的东西,但有很多年纪大的作家,随着年龄的增长,文章的思想性加强了,但是没有文采了,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才华减退了,还是取向变了。您怎么看?
韩少功:
文采首先要定义一下。文采不是那些华丽的辞藻,不是眉来眼去,它是一种韵味。语言可能很朴素,但有打动人心的力量,就是好文采。普通的词用精准,然后还有画面感、音乐感,就是好文采。
胡竹峰:你们现在还注重文章的好看吗?
韩少功:
当然了。文章首先是要好看,能感染人,打动人。讲道理是第二位的要求,很多道理大家都可以讲,讲了几千年了,贪污的还是贪污,犯罪的还是犯罪。所以文章讲道理虽然也很重要,但应该还不是最主要的,文章首先是要你能接受它,感觉得到亲切,能够感染你,打动你。我们的前辈就说过“言而无文,行之不远”。
何立伟:
我写过诗,但我写诗是不及格的。但这不影响我喜欢诗意的东西。中国是泱泱诗国。刚刚老韩讲了,第一部文学总集就是《诗经》,诗不但影响了文学,还影响了人的生活方式。诗是一种审美,是文学里最高的一种审美。你的文章,你的小说有没有诗意,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审美标准。诗不是表面的东西,不好说,比如元稹有一首《行宫》:“寥落古行宫,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。” 20个字,一幅画面。从小进宫的小宫女老到白了头,历经了多少时光,她们在闲聊摆旧的时候,还在说玄宗的开元盛世。这里面经过了几个时代,从开元到天宝,还有安史之乱,历史的沧桑巨变就在这几个白头宫女的闲谈中,这就是大诗意。这个诗意多大呀,所谓诗意,就是境界。大境界是诗意,有时候不一定是大境界,也有诗意。比如周作人形容废名的小说像弯弯曲曲的一湾水,碰到一根水草,一块石头,也要轻轻抚摸一下。这个抚摸就是诗意。闲笔出诗意。诗意有多种理解,文章有没有诗意,就看作者对审美的要求,不是一般人能写出诗意的,不是写几个诗意的句子就是诗意,它不是一种表面的东西。我说过,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多多少少带点诗的腥味,像鱼的腥味一样,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。

丛林:蔡测海老师您也上台说一说好不好?您的一本《家园万岁》还在我们这边呢。
蔡测海:
很多年没有谈过文学了,感觉又回到了八十年代。竹峰的这本书我没读过,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,知道他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优秀作家。他能够遵从古典的文化传统。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很大气的,要继承和发扬。对传统的继承越多,实践越多,生命感悟越多,表达也就越有广度和深度,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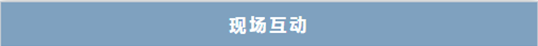
-1-
现场观众一:我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写作者,想请问一下三位老师对当代儿童文学的看法。
胡竹峰:
我也看过一些儿童文学,有些文章里面的造句、语言差得一塌糊涂,你们能让你们的小孩去看这样的书吗?所以我蛮期望有大作家来写儿童文学。现在中国有一个不好的现象,就是有一部分写文章写得不好的,就去写儿童文学,编一些很拙劣的故事来哄小孩。我也有小孩,我给他选读物的时候,我还是喜欢给他看一些西方的,古典的, 经过时间淘洗的东西。讲一句题外话,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书会,旁边有几个儿童文学作家在聊天,他们在谈什么,他们在谈怎么搞成教育局局长,怎么搞成校长,你的书卖了800本,我卖了300本,我真是吓了一跳。我对儿童文学还是蛮担忧的。小孩是很好欺骗的,他没有分辨力,不好的作品就容易对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种特别阳光特别美好的文本出现。儿童文学非常好,也非常伟大,我不是说儿童文学不好,而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家出了问题,而不是对儿童文学有成见。
-2-
现场观众二:请问韩老师怎么看驻校作家进中小学校园的这种制度,您觉得驻校作家应该给中小学生怎样的帮助。
韩少功:
我当过一个大学的驻校作家,说实话,我一直没当出什么感觉。当然,驻校作家能和学生有一些交流,讲座,上课,但到底对同学们有多少影响,有什么真正的好处,我不知道,不确定,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麻烦。我在某大学驻校呆了两个月,有一次一个大学生拿了一张语文试卷来找我,其中有一道题目牵涉到我的一个作品,下面有标准答案ABCD,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。学生就问我,韩老师这是你自己的文章,你说哪个正确?我看了一下,我觉得四个都正确呀。可你说我要是这样对学生说不是就同老师对立起来了,这不是添麻烦不是捣乱吗?所以我说驻校到底有多大好处我真是一点都不确定。这里面可能有一点其它的动机,学校想把自己的名声炒作得好一点,找一点名人来,比如电影演员啦,大艺术家呀,画家作家什么的,就可以让他们的学校名气大一点,吸收好一点的生源。香港的某些大学就会这样做,有一次香港大学一位老师来接我的时候,递给我一张名片,我一看:推广处处长。吓一跳,想大学还有什么推广处。可大学就是有推广处。你刚刚说到中学作家驻校,可以尝试吧,让作家和青年多发生一点关系,也许双方都会受益的,这是我主观的一个愿望。
-3-
现场观众三:请问胡竹峰先生,对《中国文章》这本书,您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怎样的。
胡竹峰:
我没有理想的读者,但我有害怕的读者。比如韩老师、何老师,还有在座的一些前辈,我特别害怕这些前辈看我的作品,他们目光如炬,他们太厉害了,我怕被他们一眼看穿了。我没有想过我的理想读者是谁,有时候逛书店,看到有人在那儿掏钱结账,买了我好几本书,我就觉得他是我的理想读者。我有一点跟木心是很接近的,木心说他的理想读者是伐木工人、邮递员、菜贩子这些人,其实我也一样,我希望我的读者是很泛的,并不是只有作家,评论家。
-4-
现场观众四:韩老师刚才说写文章要尽量写熟悉的人,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。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您《爸爸爸》这本书,书中这个主要人物你熟悉吗?有原型吗?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这个人物只是一个文化符号。
韩少功:
表面形式很夸张,很荒诞,但里面的几个人物其实是有原型的。原型人物叫炳伢子,就是我的一个邻居。我当知青的时候是在汨罗,住在大队部,我隔壁住着一个接生婆,她有一个智障儿子,就叫炳伢子。他只会说两句话,一句就是见到谁,只要是个男的,就叫“爸爸”,搞得人家很难为情;另一句话就是骂人、骂娘,一辈子就这两句话。长到十七八岁,还是一个侏儒。 我小说里面这个人物,几乎是写实。其它一些人物,也都有影子的。
-5-
现场观众五:韩老师好,有人喜欢拿您的《马桥辞典》和《哈扎尔辞典》比较,您怎么看待您的《马桥辞典》和《哈扎尔辞典》?
胡竹峰:
这个问题我来插两句。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可比性,只是书名都有“辞典”两个字,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。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特别委屈韩老师的,一个是说《山南水北》是中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。《瓦尔登湖》就没有《山南水北》好看,《山南水北》有人的故事, 有人的命运在里面,《瓦尔登湖》没有。《哈扎尔辞典》也没有《马桥辞典》好看。
韩少功:
西方小说是戏剧的传统,中国小说没有。散文是中国的大传统,明清小说都是从散文脱胎而出,里面还有很多散文的影子。所以胡适先生根本不承认四大名著都是小说,按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衡量,就觉得那都不算是小说。欧洲小说戏剧性的结构不是我的所长,我有时候也比较笨,要编出一个戏剧性的大起大落起承转合的大故事,我干不了,我想承接一点散文的东西,所以不经意就写成了《马桥辞典》这样了。
-6-
现场观众六:韩老师何老师你们都是对汉语有重大贡献的作家,你们都是从文革走过来的,韩老师您是知青。按理说,我们的汉语应该是有问题的,你们的文学起点应该是那种标语、口号。我想知道,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把汉语写得这样炉火纯青的?这是天份所在,还是有特殊的训练在里面。
何立伟:
昨天还和竹峰谈到木心。木心七几年才离开大陆到美国去,可以说是一个老童生,他经受过文化的大变革,但他的语言感觉完全没有受过这种影响,只能说明他有自身很强的文化抵抗力,有自己的语言自觉,我相信他是拒绝阅读狗屁的,只读好东西,只读经典。
韩少功:
你有了中国古典文章的修养以后,写白话文会有不自觉的变化。比如这个句子该长一点,短一点,怎么用词,就会不自觉受到宋词长短句节奏感和音乐感的影响。
-7-
现场观众七:韩老师,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刊物该怎么走。现在很多刊物就是几个主编自己定了一个审美标准,就在那个小圈子里的走,导致一些有点异类的作家不容易出来。这是不是我们编辑应该反省的。
韩少功:
要办好一个刊物,得一个团队都有统一的思想。刊物有很多难处,首先要生存,印刷机一开动就要钱,这个不能书生气。再者刊物要有魂,要知道刊物要干什么,不能小圈子勾兑,现在有很多编辑都是人情往来。有一部分是追着名人跑的编辑,这已经算是很尽责的编辑了,但这离好刊物很远,好的刊物要有灵魂,要有编辑思想,要有价值观。要在生存下来的前提下,坚持自己的美学思想,坚持自己的价值观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